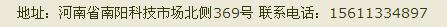实录ldquo我就是那个和母狗结婚
文/静月如许
“这孩子真有出息,还真给家里面争气。”爸妈去参加完升学宴回来口中止不住地赞叹:“可不是!重点大学呢,老徐家夫妻两个可算是苦尽甘来了。”
那时正是大二的暑假,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打发无聊的时光,听见爸妈说的话便随口问了一句:“谁呀?”妈妈取下了黑色的斜挎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在:“估计你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还小,还刚上小学呢。”爸爸在一旁道:“我记得老张家儿子那时还给人家取个外号,叫‘臭皮蛋’。”
臭皮蛋!
若我这二十年来也曾真实地见证过一次赤裸裸的欺凌的话,故事的主角就是我爸爸口中的臭皮蛋——那个弱小的、不敢反抗的被欺凌者。
我抬头望着天花板上不停旋转的吊扇,思绪也随着吊扇不断旋转,回到了我初次见到臭皮蛋的那天。
那时,他正被三个个子比他高的男孩子围住,为首的是我们镇上的“小霸王”张金。镇上年纪小的孩子们都怕他,我也怕他。但他只敢欺负那些外地来的孩子,若是欺负了本地的孩子,那孩子的父母总要跑到张金的家里面去闹上一通才肯罢休,张金回家就免不了一顿皮开肉绽。久而久之,他专挑那些外地来的孩子下手,那些孩子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且因为父母是从外地来的,大多时候也不得不低头。更多时候,受欺负的孩子们是不敢回家去告诉父母的,因为下一次可能会被欺负得更狠。
六年级的张金手下跟着两个五年级的小弟,他们一放学就在学校门口挑合适的对象,收取“保护费”。
“臭皮蛋”此刻正被张金三人围堵在一间荒废许久的石棉瓦房的屋檐下。
“你们家连衣服都买不起,就知道穿别人剩下的,收破烂!”
“你们家住的也是张金家的房子,赶紧滚出去!”
他们一个拽着“臭皮蛋”的袖子,一个扯着他的衣领,张金则“刺啦”一下拉开“臭皮蛋”衣服上的拉链,让他“脱下来”。
原来这衣服是张金的后母送给“臭皮蛋”的,张金的后母是个心善的女人,见“臭皮蛋”在冬天小脸被冻得通红,便将衣柜底下张金小时候穿过的旧衣服搜罗出来给了“臭皮蛋”的母亲。张金自幼就是个小胖子,衣服都十分宽大,“臭皮蛋”瘦小的身板穿着张金儿时的旧棉衣显得那么奇怪又滑稽,像是偷穿了大人衣服一般。但若使人一见他那皲裂的、缩在袖子里仍冻得发抖的双手,便只有苦涩酸楚之感。
看见这一幕,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我步子不自觉地慢了下来,虽然我也害怕张金,但儿童那种“好奇”和“凑热闹”的心理促使我慢了下来。
“看什么看!再看打你!”
“别以为你是女生我们不敢打你!”
“有本事你回去告啊,你看我们怕不怕!”
6岁的我那里见过这样的场面,被他们几句话就吓得双腿发软,差点哭出声来。那时的我那哪里会想,“臭皮蛋”比我还要小,被他们欺负的时候该是怎样的无助和害怕,回家后不敢告诉父母只能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的样子该是多么令人心疼。那时的我没有勇气和能力站出去帮助“臭皮蛋”,如今的我徒然懊恼和谴责自己当初的无知和懦弱。
那年,我6岁,刚上2年级,“臭皮蛋”比我还要小一岁,而且因为是外地户口,“臭皮蛋”不能在我们镇上上学,他便留在家中帮爸妈做一些家务活儿。
“臭皮蛋”的父亲是个水泥匠,常年都穿着一套灰蓝色的劳保服,上面布满了结块的水泥斑点,脚上是一双被磨出了好几个洞的军绿色解放鞋。他在镇上做零工,妻子给他打下手。他们在镇上租了一间二十平不到的房子,床、桌子、火炉、锅碗瓢盆,全都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原本雪白的墙早已经被油烟和陈年遗留下来的污垢熏得黑黄黑黄的。那房子是张金儿时住过的地方,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张金家里也建起了三层的小平房,老房子便低价租给那些外地来的工人们。
张金从心底里不喜欢这些外来人员,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他妈的!外地人没得一个好东西!”张金的父母并没有离异,他母亲是跟人家跑的。
当时的镇上没有照相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背着相机的男人来镇上专门帮人照相。最常来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穿着军绿色马甲的年轻男人,多年以后,我对这个人唯一的印象就是他身上刺鼻的古龙香水的味道。每次男子一来,身边总会围着一群女人们,她们有的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有的只是憨憨地笑,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凑热闹,许多孩子哇哇哭闹的模样就在相机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了。
张金的亲生母亲就是和这个背着相机走街串巷的男子跑了,只留下一张出自照相男之手的照片,照片上张金的妈妈烫着大波浪,穿着时髦的黑色过膝长靴,怀里抱着的张金呀还没长全,只是将手指含在嘴里,咧开嘴,不知是哭还是笑。
张金的爸爸在镇上开了一家汽修铺,给别人修电动车、摩托车,也修自行车。张金的后母是汽修铺对面开小卖部的寡妇,张金的父亲时常照顾她的生意,炎炎夏日,那女人也会为做汽修的老张递上一瓶冰镇矿泉水。张金父亲的老婆跟人跑后,老张精神消沉了一段时日,小卖部寡妇是不是会过来安慰他几句,那一声声“张哥”,让张金的父亲心底顿生一股暖意,生活的希望也重新被点燃。不久,他们重组了一个家庭。
由于“臭皮蛋”一家是外来人员,租的又是张金儿时住过的老房子,加之“臭皮蛋”父母外出做活儿,张金的后母偶尔也会帮忙照看一下“臭皮蛋”,她有时还会让“臭皮蛋”叫张金“哥哥”。“臭皮蛋”很听话,张金却不屑一顾。他本就无法接受这个后母,她以“母亲”自居,妄想管束自己,她还把自己小时候的衣服送给了“臭皮蛋”,张金从心底里讨厌这个女人。但她是大人,他是孩子,张金也无可奈何。
而对于“臭皮蛋”,张金并没有因为他的听话和软弱而与他和睦共处,反而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地欺负他、羞辱他。我就曾亲眼见过张金让“臭皮蛋”从他们的胯下钻过去。
有一次,他们说要给“臭皮蛋”一点“奖励”。那是一个被扔在路边的,没人要的矿泉水瓶,上面的塑料标签已经被撕掉了,被路过的行人踢来踢去,我上学放学时还曾用脚踢过那个瓶子,现在那个瓶子里面装了半瓶多的黄色液体。张金说那是“饮料”,送给“臭皮蛋”喝。
“这是很好喝的饮料,给你喝,你喝了就放你回家。”
“臭皮蛋”乖乖听话,把那装着半瓶尿的矿泉水瓶凑到嘴边,仰着头便喝了好几口。张金和他的两个小弟在一旁止不住地笑,问“臭皮蛋”:“好喝吗?”
“臭皮蛋”的表情木讷、呆滞,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他似乎知道一切,但是,别无选择。
“臭皮蛋”一家搬到小镇上的时候,正是计划严查的当口,“臭皮蛋”的母亲是怀着孕来到小镇上的,由于她身材比较瘦小,加之常年穿着和丈夫一样的灰蓝色劳保服,便更加使人难察觉她怀孕的事实。
“臭皮蛋”母亲生产的那天傍晚,他的父亲带着母亲躲到了附近的山上。只留下臭皮蛋一个人在家看家,家里的火炉上还炖着一锅给“臭皮蛋”母亲补身体的鸡汤。父亲临走前叮嘱“臭皮蛋”自己一个人在家要锁好门,还要照看好这锅鸡汤,如果饿了,就用一些鸡汤拌着饭锅里剩下的冷饭吃。“臭皮蛋”很听话,不哭也不闹,一直安静地坐在火炉旁守着这锅鸡汤。偶尔他也会站起来,踩着小木凳子透过窗户看着远处的山坡,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在那里。
张金和手下几个小弟路过“臭皮蛋”家门口,“臭皮蛋”的小脸正贴着玻璃窗户,两只眼睛正对上张金和他身边两个小弟的视线,“臭皮蛋”的眼里尽是惊恐。张金的小弟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儿,不知贴在张金的耳旁说了些什么,张金朝“臭皮蛋”微微一笑,示意他开门。
十分钟后,他们三人得意洋洋地端走了“臭皮蛋”父亲给母亲炖的鸡汤,其中一人临走时还不忘回过头朝臭皮蛋吐了口水,对着“臭皮蛋”竖起了中指。
“臭皮蛋”不知道生孩子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那锅鸡汤对于刚生完孩子的母亲的重要性。他只知道,只要把鸡汤给了张金他们,他们就不会打自己了,说不行就会有好几天不会欺负自己了。一锅鸡汤能够让自己少挨打,那很值得。
还没有窗户高的臭皮蛋躲进了他那二十平不到的家,透过门缝看着张金三人远去,然后关上了门,夕阳的最后一丝光线就这样被拒之门外了。
凌晨大概五点的样子,“臭皮蛋”的父亲回来了,熟睡中的“臭皮蛋”被他的父亲从床上拖到了地板上,高粱苗编织的扫把“啪~啪~”地打在“臭皮蛋”小小的身体上。“臭皮蛋”刚开始只是躲,像一只无家可归还要被人类棍棒加身的流浪狗一样拼命地去找能够藏身的角落,然后蜷缩在角落里。
看着饭锅里面的剩饭还在,而鸡汤和汤锅却没了踪影,“臭皮蛋”的爸爸喘着粗气,眼里满是质疑和愤怒:“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大人不在家居然偷吃家里面的东西!”
旁边起得早正蹲在门口刷牙的邻居看不下去了,就在旁边劝和:“老徐,孩子不懂事儿……”
就在邻居说话的这几秒钟,“臭皮蛋”跌跌撞撞地扑到了父亲的脚下,叫他:“爸爸……爸爸……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臭皮蛋”的父亲看着眼前瘦瘦小小的孩子,他的眼神是那样无辜,含着泪不停地啜泣,用两只袖子交互擦拭着脸上的鼻涕和泪水,就连哭,他都不敢大声哭出来,他是一个那样乖的孩子啊。父亲的心顿时就软了下来,却罚他中午不准吃东西,晚上把地扫干净才能吃晚饭。
那件事过后的一个多月,“臭皮蛋”一家搬走了。
某日的黄昏,“臭皮蛋”父亲干完活回家的路上,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孩子被张金几人欺负的一幕。那是一个用稻草和几块烂木板简单拼凑成的狗窝,“臭皮蛋”小小的身体整个倒在狗窝里,他的背后还躺着一只一动不动的老狗,身上散发一股刺鼻的臭味儿。老狗似乎已经习惯了镇上小孩子们时不时的戏弄,朝它扔小石子儿更是家常便饭,它懒得动,因为它知道等它转过身来,这些捣蛋的孩子早就一溜烟儿跑远了,所以就连老狗也懒得理会他们。
躺在狗窝里的“臭皮蛋”和老狗一样,都是这个镇上的弱势群体、被欺凌者。或许他们也曾反抗,也想反抗,后来明白反抗无用,便只能默默忍受。
张金几人像看喜剧一般在旁笑个不停。
“这样,你就算是和母狗结婚了。”
“哈哈哈……”
“臭皮蛋和母狗结婚了。”
“哈哈哈……”
同样的手段、同样的方式,但在一个父亲看来,那是用利刃、用烈火、用滚油来煎熬他的心。“臭皮蛋”的父亲,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永远也不理解,一个六年级的大孩子何以会做出如此恶毒残忍的事情。
也是在那一天,他知道了“鸡汤事件”的原委。这个时候这位老实巴交的父亲才知道,他的儿子“臭皮蛋”在挨打的前一天就已经整整一夜都没有吃饭,自己第二天还误会了他,狠狠打了他。不知道打他的时候他饿不饿、痛不痛,是不是很恨这个父亲……
“臭皮蛋”的父亲弯下身在狗窝旁边捡起那口被张金他们扔掉的、已经微微变形的小锅,抱起“臭皮蛋”,把他背在自己那因为常年弯腰做活而再也挺不直的背上,朝张金父亲的修理铺走去。
这个外来务工的农村人一直老老实实,从不挑事儿,不论干活还是做人一直都是本本分分,就算是自己有理他也很少去和他人争论,因为自己是“外乡人”。
那天晚上,张金的父亲用皮带狠狠地抽了张金,张金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也不再去上学了。
第二天,“臭皮蛋”一家搬走了,“臭皮蛋”的父亲在大家面前说是要回老家给小的那个孩子上户口,而且“臭皮蛋”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但是镇上的人在背后不止一次议论,“臭皮蛋”一家因为和张家闹掰了,被张金的父亲“赶走”的。不过一段时间之后,“臭皮蛋”一家也被逐渐淡忘了。有人离开,有人回来,有人路过,镇上的人们永远不乏新的话题。
他们一家搬走后的第四年,张金摔死了。
那年张金15岁,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非但烟酒从不离身,而且彻夜不归更是家常便饭,偶尔回来一次不是一身酒气,就是带着许多衣着奇怪、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少年少女在家里过夜,把家里糟践一气后第二天有说有笑地离开。
看着张金的后母弯着腰收拾“残局”的样子,张金的父亲生了大气:“让他在外面混!最好一辈子不要回来,当我没有这个儿子!”
三天后,张金的父亲把楼上楼下的房间全部换了锁,也正是他换锁的那天晚上,张金回家了,眼见着自己的钥匙打不开家中的门他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他没有敲门,也没有大声叫父亲给他开门。十几岁的年纪,正是最叛逆的时候,就算父亲换锁,也难不倒他张金,只要他想回家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望着那根白色的从三楼窗户外一直延伸到一楼,并被埋入地下的、比他手臂还要粗的厕所排水管,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凭借着自己在外面打架的“经验”,他自以为身体十分灵活,便顺着排水管开始往上爬……
待到第二天邻居在楼下大喊“老张!快下来,出事儿了!”的时候,张金的身体已经冰冷了。那个帮人修了三十多年车的男人打开一楼的铁门,衣服还没穿好,裤子刚拉好拉链,最后一科扣子还没来得及扣,望着眼前的一幕便直直地扑了过来,怀里紧紧抱着他那身体冰凉的儿子:“救护车,快叫救护车!”,情绪很不稳定的老张向邻居求助,有的邻居在帮他拨打急救电话,更多的是无奈地摇头。
最终,张金的父亲一脸无助地瘫软在地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不可一世、目中无人的小霸王张金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我原以为他会一直横行,变成“大霸王”、“老霸王”。
很多年后,我也没有想过妈妈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臭皮蛋”的母亲,并被邀请去参加升学宴。
如今的小镇早已变了当初的模样,来去熙攘的人群和车流从未间断,不知多少故事在其间流转。
小糯米是好姑娘买猫儿的路程缩短1cm
转载请注明:http://www.xyzs168.net/xszy/17935.html